1936年10月19日,鲁迅在上海逝世。八十余年过去,他锐利的目光穿透纸背,依然注视着我们赖以生存的这片土地。
倘若说鲁迅有什么“接头暗号”,那大概不是某本书,而是他笔下那些永远鲜活的人物形象——看到月光会想起“一轮金黄的圆月”,吃茴香豆会琢磨“茴字有四种写法”,遭遇不公会默念“勇者愤怒,抽刃向更强者;怯者愤怒,却抽刃向更弱者。”
今天,让我们一同回望鲁迅的书单,走进那四部在他生命中留下深刻印记的著作。正是这些跨越时空的对话,参与构建了鲁迅的文学品格、哲学思想与战斗精神,最终汇成了那道穿透历史迷雾的不朽光芒。
PART.1《山海经》
在《阿长与〈山海经〉》中,鲁迅深情回忆了童年收到这本宝书时的喜悦:“我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,全体都震悚起来。”那本刻印粗拙的《山海经》,成为他最早接触的奇幻世界。
人面的兽、九头的蛇、三脚的鸟、生着翅膀的人……这些怪诞神奇的意象不仅满足了孩童的好奇心,更在作家心中埋下了想象的种子。日后鲁迅作品中那些奇幻诡谲的梦境描写,那些对“牛首阿旁,畜生、化生”的地狱想象,依稀可见《山海经》的影子。
他说:“这四本书,乃是我最初得到,最为心爱的宝书。”
PART.2《聊斋志异》
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高度评价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:“花妖狐魅,多具人情,和易可亲,忘为异类。”这种对鬼狐人格化的处理,深深影响了鲁迅的创作。
在《铸剑》中,黑衣侠士的神秘形象、眉间尺自刎献头的决绝,都暗含《聊斋志异》式的怪诞与壮烈。鲁迅笔下,那些看似荒诞的情节背后,往往隐藏着更深层的真实——正如聊斋中的鬼狐,反而比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更有真性情。
PART.3《水浒传》
鲁迅对《水浒传》的感情复杂而深刻。他既看到梁山好汉反抗压迫的合理性,也洞察到这种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性。
在《三闲集·流氓的变迁》中,他精辟指出:“侠”字渐消,强盗起了,但也是侠之流,他们的旗帜是“替天行道”。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,不是天子……所以大军一到,便受招安,替国家打别的强盗——不“替天行道”的强盗去了。终于是奴才。
这份清醒的认知,让鲁迅在赞美反抗精神的同时,始终对革命异化保持警惕。他对《水浒传》的解读,至今读来仍发人深省。
PART.4《西游记》
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谈到《西游记》:“作者禀性,‘复善谐剧’,故虽述变幻恍忽之事,亦每杂解颐之言,使神魔皆有人情,精魅亦通世故。”
《西游记》这种“幽默中见真谛”的笔法,在鲁迅的创作中得到了创造性转化与发展。他善于用幽默讽刺的笔调揭露社会黑暗,用诙谐轻松的语言讨论严肃话题。《西游记》是“向西取经的征途”,鲁迅的一生亦是:一辈子“横站”于乱世,向禁锢思想的“铁屋子”奋力挥棒。
四部经典,构筑了鲁迅丰富的精神世界。在这些传统文本中,他汲取的从来不是僵化的教条,而是批判的勇气、想象的自由、变革的力量。当我们重读这些经典时,或许能更贴近那个始终与我们同行的灵魂——正如鲁迅先生所言:“无穷的远方,无数的人们,都和我有关。”
-完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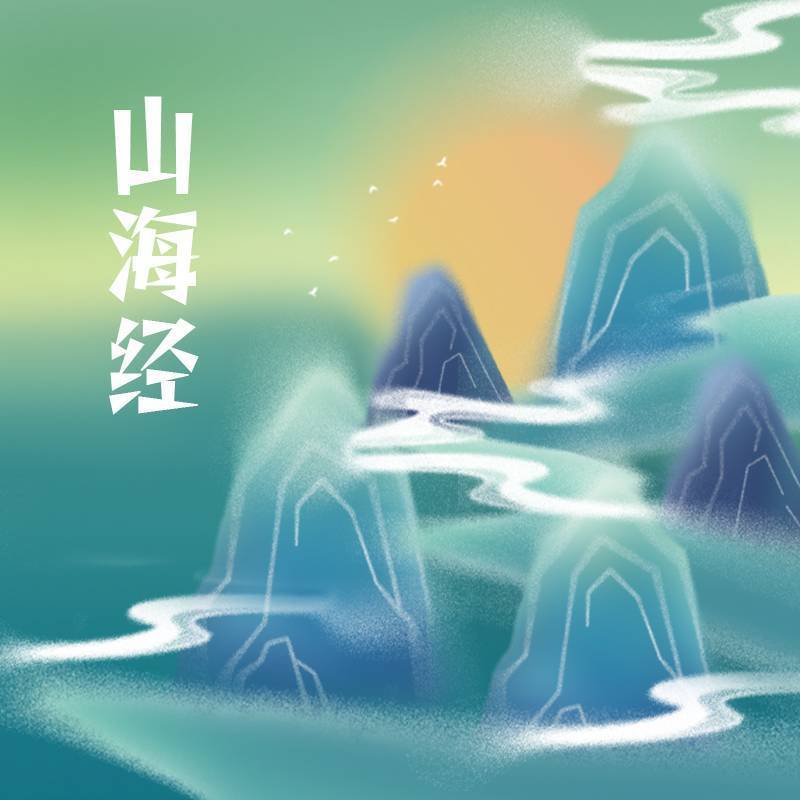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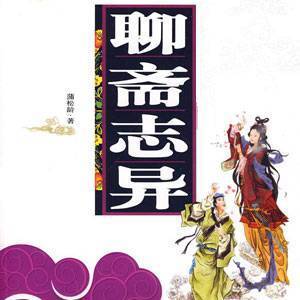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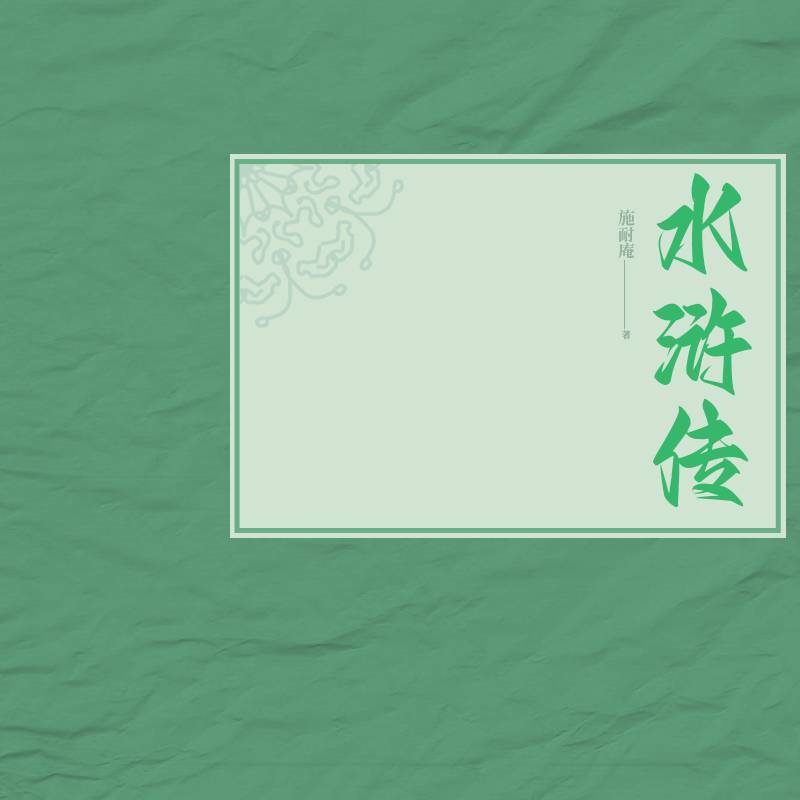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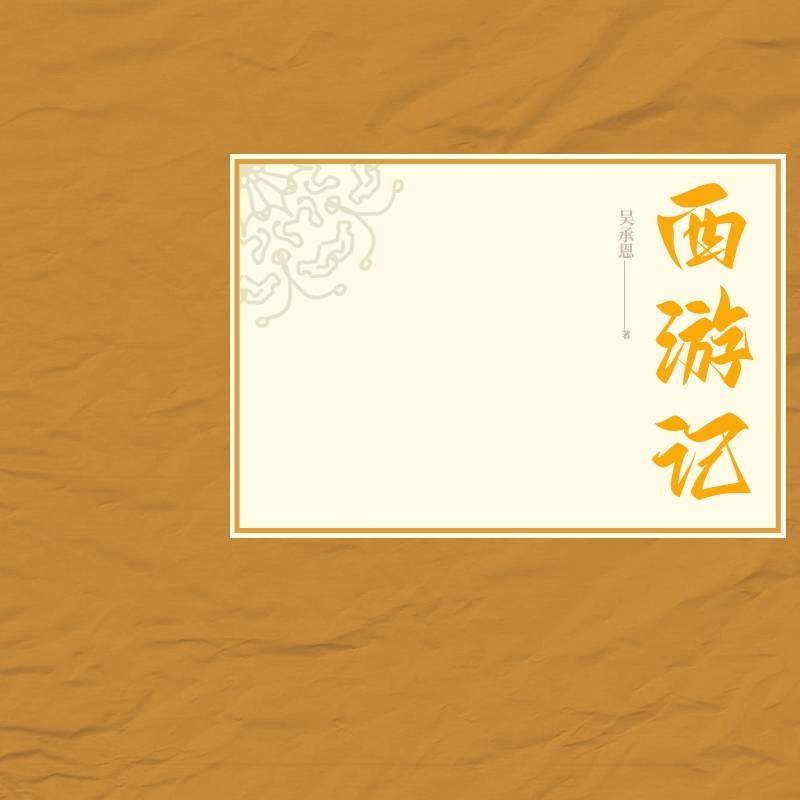


 渝公网安备 50022702000145号
渝公网安备 50022702000145号